胡适论禅宗曾说: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八世纪到九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佛教极盛时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
胡适讲禅宗,一再使用“革命”这个概念。特别是讲到南宗,他称之为“南方新佛教” ,“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认为“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禅教的一种革命” ,等等。他特别强调指出禅宗乃是佛教“中国化”的果实,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钱穆介绍禅宗也说:
唐代禅宗之盛行,其开始在武则天时代,那时唐代,一切文学艺术正在含葩待放,而禅宗却如早春寒梅,一支绝娇艳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开出。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洒脱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所以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
这是钱穆《中国文化史》里的一段话,他特别赞扬禅宗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贡献,同样使用了“革命”一语。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也说过:“修行不必在寺”再加上“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不必外求,这又使禅宗的立场和新教的“惟恃信仰,可以得救”十分接近。如果“个人与超越真实之间的直接关系”(The direct 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ranscendent reality)确是近代型宗教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禅宗和基督教无疑同具有这一特征……禅宗也是把人的觉悟从佛寺以至经典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认为每一个人“若识本心,即是解脱”(《坛经》语)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至少不能不承认慧能的新禅宗确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运动了。
不仅中国学者谈禅宗“革命”,日本学者也有类似意见。柳田圣山是禅史研究的大家,他说,禅宗乃是由“印度传来的教相判释的佛教向扎根于中国民族特有的宗教意识的祖统佛教的全新的转变”。他又说:
对于所谓“禅宗”的形成,作为其革命的动机的,不正是作为最上乘的般若主义,特别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立场吗?
不言而喻,上述几位所谓“革命”,不是指政治革命,是指佛教发展历史上重大的、带有根本意义的变革。禅宗是彻底“中国化”的佛教,是真正意义的“中国佛教”,一方面,它确实是中国长期发展的佛教产生真正巨大变革的结果;另一方面,禅宗自诩是“教外别传”,是“以心传心”,是真正体现“佛心”的佛教,这作为宗教潮流就确有“革命”的意味。把禅宗看作是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中的“革命”,是对它的性质、意义、价值和贡献的合乎实际的判断。
这个“革命”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对于认识中国佛教的历史,对于总结佛教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佛教的发展等等都具有根本性质的启示意义。
从印度输入的佛教在中土扎根,真正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广泛影响,是从两晋之际开始的。当时困于儒家章句和玄学思辨的文人士大夫,接触到具有丰富、新鲜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的外来佛教,真是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中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佛教,佛教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上扎根、发展并逐渐实现“中国化”。斯坦因说,“古代印度、中国及希腊诸种文明相互交流融合……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 。佛教输入中土,实现了中、印两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造成的影响、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是极其巨大的。这些都详著于佛教史、文化史,此不具述。
自佛教输入中土,就步入“中国化”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体现为各民族文化传播中一般的所谓“民族化”,而是在中国民族土壤上从性质到形态的根本变革(关于这个问题,争论颇多,这里不拟展开讨论)。其中具有关键意义和作用的一方面,就是外来佛教适应中国专制政治体制,宗教神权服从世俗政权,从而从信仰到组织、从思想观念到生存形态发生了全面变化。道安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即表明当时的佛门领袖已经清晰地自觉到必须受庇又服务于专制皇权才有出路。因此,伴随着外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其“御用化”程度不断加深。佛教从而逐步融入到中国专制政治、社会体制之中。这必然带来佛教发展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到齐梁时期,如从东晋立国算起仅仅过了一百几十年,佛教主流部份的腐化程度已十分严重,其内外矛盾已经成为南北王朝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当然,南北诸王朝的破灭有诸多原因,但是佛教势力膨胀、统治者佞佛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专制必然带来腐败,佛教僧团也是如此。
东晋僧人道恒的《释驳论》已经描述当时的僧团“营求孜汲,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抵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 。到齐、梁时期,帝王佞佛,权贵好佛,成为风气。梁武帝作为“菩萨皇帝”,是历史上佞佛君主的典型。他在位时期,有郭祖深,为南梁郡丞,徙后军行参军,曾舆榇上书,中谓: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这是激烈指斥僧团膨胀的危害及其腐败。他又有封事说:
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也。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论外则有勉、舍,说内则有云、旻。云、旻所议则伤俗盛法,勉、舍之志唯愿安枕江东。
这里的“勉、舍”,指徐勉、周舍,都是佞佛大臣;“云、旻”则指光泽寺法云、庄严寺僧旻,均列名梁武帝朝的“三大法师”之中。他把矛头直接指向这些教内外领袖人物,实则在指斥皇帝本人。另有荀济,与梁武帝本布衣相知。及梁台建,不得志,常怀悒怏二十余载,见梁武佞佛,寺像崇盛,以八十高龄上书,指斥佛教贪淫,奢侈妖妄,又讥刺建造同泰寺营费太甚,必为灾患。长长的表章是对佛教弊害十分详尽的揭露和抨击。如钱锺书所说:当初周朗、郭祖深等人批评佛教,“并非辟佛废释”,“只斥僧寺之流弊而不攻佛法为异端”,荀济则“一概摈弃” 。这后一篇奏章人们耳熟能详,此不具引。北朝的情况亦类似。神龟元年(518),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519)鉴于“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曾上表谏诤削减营造,节省功力。他本是虔诚的信仰者,揭露佛教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意在加以整肃。在他去世前一年,更长篇论奏,专事揭露私造寺庙,滥度僧尼的弊端,其中说:#p#分页标题#e#
……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薰莸同器,不亦甚欤!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喧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何以劝善……这是一位虔诚信仰者同时又是统治阶层一员提出的看法。包括其中指出的太和年间法秀“大乘匪”利用弥勒信仰的叛乱,揭露佛教无限制膨胀造成的社会危机。至于庞大的寺院经济对于民众的侵夺,对于国计民生的损害,文献里有众多材料,亦毋庸赘述。总之,佛教的腐败不仅成为众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对于专制统治体制已造成严重弊患。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佛教教理在中国思想学术环境中发展,形成一批义学师说即中国独创的学派。南北朝时期具有高度内外学素养的义学沙门的义疏之学,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都对中国思想、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其价值与意义是必须给予充分估价的。但这是上层僧侣的脱离民众信仰的经院学问。本来对于宗教来说,教理的说明与论证是为树立信仰服务的,可是这种高度形而上的思辨形态的义学师说却成为信仰的反动,终究也是思想贫乏的表现。顾随曾说:
……宗教哲理,陈义愈高,析理愈细,即索解愈难,去人愈远;而其自身亦由是而孤立,而衰颓,而澌灭矣。
而另一方面,民间盛行的保守的禅修则宣扬、鼓吹神通灵异。如玄高“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后来被摈斥到河北林阳堂山,徒众三百,禅慧弥新,据说“磬既不击而鸣,香亦自然有气。应真仙士,往往来游。猛兽驯伏,蝗毒除害”。玄高学徒之中优异者百有余人,其中玄绍,“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据说也灵异异常,“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而玄高门下灵异如绍者更有十余人之多 。这种低俗的迷惑民众的手段,是与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相违背的。
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理等种种层面,到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都陷入困境,面临挑战。佛教的这种发展形势显然严重背离了佛陀创教的本怀,脱离了群众的信仰需求。这种状况受到教内外的批判与抨击,也引起某些世俗政权的限制和弹压。在后一方面,重大的打击是北魏和后周两个王朝先后禁毁佛法。当然,两个朝廷毁佛的起因很多,但佛教自身的腐败应是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在佛教内部也出现了摆脱危急与挑战的努力。典型的表现有三阶教、净土信仰的兴起,一批内容浅俗、行文简洁的伪经的出现,等等。它们都具有某种“宗教革命”的意味。这样,南北朝末期,佛教变革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一种潮流。教内外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佛教必须“革命”,才有发展出路。禅宗从而因应形势兴起。创建禅宗的祖师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摆脱佛教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而做出努力的。
南北朝后期已经逐渐形成由游行民间的下层僧众主导的一种革新潮流。这些人与北朝的昙鸾、南朝的“三大法师”那类御用名僧或义学沙门不同,也与玄高、跋陀、僧稠、僧实等守旧派禅师不同。在南北朝社会动荡中,破产失业的流民是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社会力量。在这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活跃在流民中的下层僧侣引导了佛教革新的潮流。为谋生路而披上袈裟的流民,不熟悉也不会热衷义学沙门的繁琐的义疏之学,他们也没有可能和机会隐居山林、坐守枯禅,他们也不会凭借宣扬灵异、炫耀神通赢得统治者的信重。他们要自谋衣食,度过朴素简单的头陀生活;他们也要把繁琐的义学思辨简单化,提倡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除了各类破产流民,还有在乱世中被逼迫到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出家为僧,会给佛教的新潮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发挥。后来被当做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实际即是游行民间的头陀僧的代表,据传他所作的《二入四行》就体现出新的佛教潮流的禅观和操守。这样一批宣扬新的禅观的新型禅僧就出现了。到隋末唐初,禅史所说的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出来,在当时还十分荒僻的长江北岸的黄梅山林聚集徒众,组成新型的僧团,就是这类禅僧的群体,一个革新的教派从而创建起来。#p#分页标题#e#
吕澂指出:
道信住在双峰山的时间那样长,徒众那样多,在史传中却看不到有什么官僚豪门的支持,而是用自给自足的方法解决生活问题,这与当时居于城市依赖权贵的佛徒是不同的。
这样,这个革新宗派,第一,不同于南北朝“御用化”的贵族佛教,它不依附、服务于朝廷、权贵,而是面向民众的;第二,这一派禅僧不再作受众人供养的“僧宝”,而是自力更生、自我修行的普通人。据传四祖劝诸门人说说:“能作(作务)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 第三,道信、弘忍师弟子弘扬的这种坐禅守心的新禅法是对六朝以来发达的义学师说的反动。第四,这种新禅法摆脱神通灵异的迷信,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性质。总之,它一举而截断众流,倡导一种“一切心为宗”的全新宗义和简单易行、直截了当的学风和宗风。这种新潮流一经出现,就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造成佛教内部的重大变革,更逐渐形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以至在后来一段历史时期里,禅宗在佛教诸宗中几乎是一家独大,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学术、文化各领域更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种新佛教的建设也是充满矛盾的。这特别体现在所谓南、北宗的斗争。概括地审视这一斗争,仍和佛教在当时发展的总体环境相关联。道信、弘忍创立的新兴宗派,在唐初动荡社会环境形成相当巨大的、关系社会安危的势力,统治者不能不采取对策,加以笼络、利用。又适值武则天阴谋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就积极地把当时声势正隆的神会及其门徒义福、普寂等召请到长安。这个新教派从而由遁迹山林转而进入宫廷。新宗派的领袖神秀成为武则天宫廷的御用名僧,他下一代的普寂等人均占据两京地区大寺,接受朝廷和重臣、宦寺的供养,以至后来南北各地的北宗一系禅师的活动,主要也得力于帝王将相的扶植和支持。这样新兴的禅宗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革新的性质。而与之相对照,慧能在荒僻的岭南开创南宗禅,则继承、发扬道信、弘忍僧团山居修道、沉迹民间的传统。慧能当初以卖柴为生,来在弘忍门下服踏碓这样辛苦的粗重劳役,实际是谋取衣食的流民。弘忍正是大量收容这类流民,才组织成规模巨大的僧团的。慧能离开黄梅,“退藏于密”,在岭南“混农商于劳侣” ,实际也是逃避赋役、四处奔波的流民身份。他终于在岭南集合数千信众,造成相当声势,其群众基础还是那些谋取衣食的流民。后来他这一派禅宗逐渐扩展势力到今四川,再后来南宗的基地也主要在湖南、江西等,基本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发展。当然,在大唐帝国领域之内佛教不可能脱离或拒斥朝廷和当权者的管辖和供养,但南宗一系显然保持更明显、突出的民众性格,更多代表社会下层的观念和利益。南宗在与北宗的较量中终于取得胜利,也是宗教“革命”再度取得胜利。杜继文说:
南宗理直气壮地以卑贱的愚民形象站立起来,同出身高贵、儒学传家的同行们公然对立,其意义大大超过了禅宗本身的范围,而与隋唐以来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一部禅宗史,也可以看成是一部社会史的投影。
禅宗“革命”让人们联想起欧洲天主教历史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或许用“宗教改革”来说明禅宗更为适宜。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看,两者确有可“比较”之处。禅宗之作为佛教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与造成欧洲新教“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多有类似之处。十五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鼓动起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罗马天主教的精神统治随之动摇。中世纪的教会不仅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科学的发展,同时对民众勒索盘剥无所不用其极,如征收所谓“十一税”和传教费、圣水费、祈祷费、埋葬费等等。特别是教皇利奥十世以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出售“赦罪符”来搜刮民财,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革新的先驱人物是捷克人约翰·胡司。他在平民中活动,宣扬“在上帝眼里,一个有道德的贫苦农民比一个富有而犯罪的教主要高尚得多”。他抨击教会的专制、腐化,反对农奴剥削制度和苛捐杂税。虽然他最终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但他播下的宗教改革的种子却滋生起来。宗教改革的首倡者是德国人、铜矿工人的儿子马丁·路德。1517年,罗马教廷派人到德国推销赦罪符,他起而率众反对,继而用拉丁文写出九十五条批评教廷、改革教会的意见书,其核心主张是“信仰可以获救”。即是说,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苦读圣经,忏悔自己,无需通过圣徒,也不需要付钱给教会,就可以“通上帝”。他要求消减教会的苛捐杂税,反对奢侈、繁琐的宗教仪式,提出建设“廉价教会”,主张读经、讲经自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得到德国世俗王公们的支持,不过受到形势发展的限制,没能深入进行下去。它所引发的一场由闵采尔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也被镇压下去了,但其影响却相当巨大和深远。到十六世纪中期,宗教改革运动以更大的声势兴起。法国人加尔文及其追随者把改革运动引向深入。他们批判天主教宗教神学,主张回归到《圣经》的立场,强调上帝对人的普遍的爱,在上帝面前人格平等、自由意志;要求人们作出努力、体面地劳作,反对懒惰;鼓励“给予”和“付出”,爱人如己;强调谦卑,认为“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始,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箴言》);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伦理原则视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泰书》)。另一方面,认为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就是朝圣之旅,在这个旅程中始终需要抵制来自罪恶世界的诱惑,作为上帝的“选民”,终究会得到进入天国的“恩宠”。这样就创造出新的教派——“新教”或称“清教”。这个革新的教派在不否定对上帝信仰的仁慈回应的同时,更加强调人的深层次的心灵体验,这是“一种深刻的、一切都归因于《新约》的个人的宗教;它与任何政府无关,也不对任何大的信徒团体的组织负有义务” ,因此它常常被称为“心灵的宗教” 。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哺育了近代的经济人。”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新教的形成和传播、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精神动力和伦理保障。#p#分页标题#e#
这样,无论是信仰平凡人的“内心”具有超越的能力而否定政治权威和“他力救济”,还是反对教会的经济盘剥而强调教团自力更生,欧洲的新教“革新”与早期禅宗都相类似。这种类似体现了人类宗教发展的普遍规律。
不过,禅宗后来的发展却与欧洲新教发展形势大不相同。经过革新的新教逐步普及到整个西欧,造成天主教历史上的大分裂;传入英国之后,给工业革命提供了精神支柱。西欧各国教会纷纷脱离罗马教廷,宗教改革从而成为资本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的一部分。新教继而普及到整个欧洲和北美,成为西方世界的民众宗教,至今仍在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如前所述,到武则天时代,“东山法门”已进入宫廷;许多禅宗大德得到朝廷礼重;中唐以后,禅宗内部发生分化,分成众多派系,这些派系大都托庇于各地强藩大镇,许多派系领袖的祖师又融入到统治阶层之中。在信仰层面,禅宗回归教门,“禅教合一”、“禅净合一”成为潮流。吕澂指出:
禅宗思想到赵宋一代,有了较大的变化……其后能继续存在的几派,都是依赖统治者的支持的,当时著名的禅师经常与官僚等周旋,接触上层人物,这就使原来禅宗居住山林常同平民接触而形成的朴素作风丧失殆尽(本来从五代以来已丧失不少),其基本思想亦积极向主观唯心论方面发展……此种思想可说是和统治者的需要契合无间的。
这样,作为宗教“革命”的禅宗实际是破产了。当然禅宗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单线的,后来的成就与贡献不可泯灭,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关于这个方面,不必赘述。但是从历史发展说,禅宗虽然传承有序,但已失去了当初的革新精神,也不再发挥当初那种积极的社会作用。
禅宗历史发展的这种曲折变化,提供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黄仁宇在评价李贽时曾说:
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它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他美术化或神秘化。
禅宗也同样,它的理论即禅思想否定方面强而建设方面弱。而究其原因,不决定于禅宗祖师们的思想境界,而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欧洲文艺复兴那种孕育新的思想理论和社会潮流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经过禅宗“革命”的中国佛教终于回归到依附世俗政权的“御用佛教”的道路上来,这也是在中土环境中佛教发展的“宿命”。
宋元以降,多数名声显赫的大僧又如南北朝那些高级沙门一样,成为社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其中不少人积极参与政治,例如宗杲参与抗金斗争、宗衍参与明初政争,他们发挥的具体作用不同,但积极参与世事则一,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上层重要成员的身份也一样。宋代以降的所谓禅寺,也失去了当初丛林农禅的精神与特色,成为盘剥民众的寺院经济实体。由于“禅净合一”成为民众佛教的主流,求福消灾、以至卖罪买福的低俗迷信流行,信仰也就失去了活泼的生机。
韦伯曾指出:
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体现的理性化阶段时,可以运用两个在很多方面互相联系的尺度。其一是,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二是:这个宗教将上帝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宗教自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
徐复观也曾说:
只有人文中的人生价值,亦即是在道德价值这一方面,才与宗教的本质相符,可以发生积极地结合与相互的作用。没有人的主体性的活动,便无真正的道德可言。宗教与人生价值的结合,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亦即是宗教与人文的结合,信仰的神与人的主体性的结合;这是最高级宗教的必然形态,也是宗教自身今后必然的进路。#p#分页标题#e#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禅宗“革命”与是欧洲宗教革新在成果、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相差得是太悬殊了。而这正体现在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之下宗教(包括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民间秘密宗教)存在的必然形态。
在当下,如何认识、阐发佛陀创教的本怀,建设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宗教、徐复观所说的“与人生价值的结合,与道德价值的结合”的“高级宗教”,仍然是具有重大挑战性的课题。百多年来,僧、俗有识之士意识到这样的形势,曾爲“振兴”佛教作出种种努力。包括居士阶层唯识学的振兴,“人间佛教”、“生活禅”的提倡,等等。这种努力直至如今迄未停止。而中国佛教的前途如何,端在看这种努力的结果如何。这不仅需要认识、观念、方策,需要僧俗共同持久的奋斗,更重要的还决定于佛教生存的社会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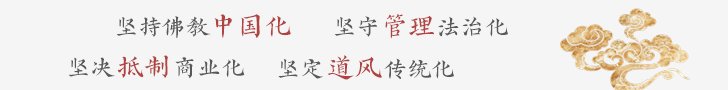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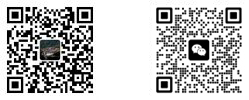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 42112702000026号
鄂公网安备 42112702000026号